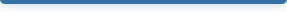◇鐘華(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
作為本土主要的核果類植物,葡萄屬遺存在我國不同區域的考古遺址中均有發現(以炭化葡萄種子的發現為主),出現時間從萬年左右的農業起源時期,一直延續至漢代以后的各歷史時期。但是,囿于植物考古的發現較為零星,學界缺乏對葡萄屬遺存的系統梳理。此外,就出土葡萄屬遺存本身而言,一方面葡萄種子難以進一步鑒定到“種”的層面,另一方面其繁殖的方式也有別于農作物,致使我們很難判斷本土葡萄屬遺存的馴化屬性,長期以來視其為野生的采集類植物資源。
在我國,無論是鮮食還是釀酒用的葡萄,多指來自于西方的歐亞種葡萄。歐亞種葡萄在西亞和歐洲有著悠久的利用歷史,目前比較明確的歐亞種馴化葡萄的考古證據來自西亞黎凡特地區的幾處青銅時代早期遺址(距今約5500年至4000年)。目前,我國歐亞種葡萄最早的證據是大約2300年前發現于新疆吐魯番洋海墓地的葡萄藤。《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齊民要術》等文獻也提到,歐亞種葡萄在西漢時期已經被帶入內地。
在歐亞種葡萄傳入我國之前,古代先民已開始利用本土野生的葡萄屬植物資源。《詩經·豳風·七月》《詩經·周南·樛木》《易經·困卦》等先秦文獻就有多處提及葡萄屬遺存早期利用的情況。葡萄屬植物有60余種,我國存在約38種,是世界三處野生葡萄集中分布的中心之一。我們認為,僅依靠葡萄屬種子的形狀特征,幾乎無法對其品種進行進一步判斷,更難以與先秦文獻中屢次出現的蘡薁和葛藟進行明確對應。
正如歐亞種葡萄在西亞地區的早期發現一樣,我國本土葡萄屬植物的考古證據也包括葡萄籽、葡萄藤(炭化葡萄木材)和酒石酸。在這三種考古遺存中,葡萄籽無疑是最為常見、考古出土數量最多、保存狀況最好的葡萄屬植物遺存。這些種子遺存的發現縱貫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到歷史時期的各個時段,相關發現也遍布我國內地的大部分區域。就保存形式而言,大部分葡萄籽是炭化后保存的,僅有少數在極度干燥或飽水的環境中得以留存。
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距今約10000年至7000年,這一時期的葡萄屬種子作為古代人群采集類植物遺存,其發現遍及各個主要的遺址分布區,但發現數量都相當有限。不同區域的種子尺寸、形狀相差不大,具備野生葡萄屬種子的性狀特點,即偏圓形的種子形狀和較為短小的喙部。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7000年至5000年,這一時期葡萄屬種子的發現在全國范圍內仍然較為常見,數量也普遍較少。有意思的是,在發現葡萄籽的遺址中,往往狩獵采集經濟依舊是重要的生計方式,成熟的農業生產體系并沒有完全確立,農業社會也未完全形成。以中原地區為例,在廟底溝時期以粟為主的成熟旱作農業社會形成之后,葡萄屬種子便幾乎不再出現。
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距今約5000年至3500年,這一時期的葡萄屬種子集中出現在黃河中下游、淮河中上游、長江下游的一系列遺址中。當時,這幾個區域都已建立了相對成熟的農業體系,狩獵采集經濟對其影響已非常有限。盡管該時期中原、海岱地區考古遺址發現葡萄屬種子的數量仍然不多,但這些種子在黃河中下游、淮河中上游、長江下游遺址中較為普遍,在新砦、二里頭等高等級都邑性遺址也都有發現。南方良渚文化的多個遺址中,不僅葡萄屬種子的發現很常見,數量也較新石器時代晚期有了明顯增多。
進入歷史時期尤其是西漢之后,西方的歐亞種葡萄開始傳入我國內地。就目前有限的考古證據而言,西漢時期可能存在西方歐亞種葡萄與本土葡萄屬并存的局面,這種狀況延續至唐宋(遼金)時期。隨著西方葡萄的傳入,本土葡萄屬并沒有立刻消失,而是繼續被發現于從東北至南方沿海的廣大區域,但歐亞種葡萄似乎更多出現在西北地區。
對于一般的果樹類植物資源,馴化的過程往往表現在果核(種子)拉長,即長寬比增大,同時基部更為尖銳,通過增大果核表面積的方式,達到單粒果實所含果肉量更高的效果。從以上多個時期不同遺址出土大量本土葡萄屬種子數據來看,不同時期葡萄籽的長寬尺寸分布范圍有著明顯的重合,長寬比也無法看出明顯的時代性變化。我們認為,本土葡萄屬種子形狀和大小的時代差異性并不顯著;西方歐亞種葡萄傳入后,本土葡萄的利用至遲延續至唐宋時期。
一般認為,我國本土的葡萄屬植物均為野生品種,目前沒有可用的本土馴化葡萄的鑒定標準。對于馴化早期的葡萄籽,不少植物考古學家認為,僅通過種子形態,無法有效區分野生葡萄和早期馴化葡萄。不過,除尺寸和形狀外,馴化葡萄屬遺存還可以通過其他生物特性和形態特征來鑒別。我國考古發現的葡萄屬植物遺存絕大多數都是炭化的葡萄籽。盡管本土葡萄屬植物經馴化后可能會出現基因方面的轉變,比如異花授粉到自花傳粉,但是目前炭化葡萄籽還難以有效提取DNA信息,因此難以判斷其授粉方式和繁殖方式。而諸如葡萄串結構、果肉含量、甜度以及是否存在未完全發育的果實等信息,現階段也無法通過考古發現來獲知,也就不能借助這些葡萄屬植物生物特性和形態特征的變化來判斷其馴化屬性。
種子本身沒有發生明顯的馴化特征,這是否可以說明中國本土的葡萄屬植物在古代一直沒有經過人工栽培?在討論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植物考古一般用馴化指代植物經由人工干預影響而形成的一種特殊進化過程,體現在植物生物特性和形態特征發生的改變;栽培則側重人類為了有利于植物生長而采取的各種行為,包括栽種、管理等行為,植物本身不一定發生性狀的變化。
盡管早期葡萄遺存的馴化屬性難以判斷,但我們認為,通過已有的多個不同角度的考古學材料,推斷葡萄屬植物栽培屬性是可行的。通過這些考古學材料,可以進一步推斷我國古代先民很可能在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已經對本土葡萄屬植物進行了強化管理和栽種,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我們以中原地區為例,對葡萄屬種子的時空分布特點進行分析。中原地區龍山時期至二里頭時期,葡萄屬種子的大量發現與狩獵采集經濟體系關系不大,也不是仰韶時代傳統旱作農業的延續,而應是一種新興的植物資源利用方式。以葡萄屬為代表的果核類植物遺存在這一時期遺址中普遍出現,我們認為這一現象可能與古代人群對水果類植物資源的強化管理乃至栽培種植直接相關。
第二,這一時期除了出土的葡萄屬種子以外,我們還發現了葡萄屬植株木炭。以二里頭遺址為例,該遺址不但發現了葡萄屬種子,其木材考古證據也顯示了炭化葡萄藤木材碎塊的存在,葡萄籽和葡萄藤的同時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遺址內或周邊存在葡萄屬植物栽種的可能。除了葡萄籽,我們在該遺址二里頭時期的遺存中還發現了眾多核果類果核,包括酸棗核、歐李核、桃核,與此對應的棗屬木炭、杏屬木炭、桃屬木炭在遺址中也有大量出土。
第三,龍山晚期到二里頭時期,多個關鍵區域社會復雜化不斷加劇,區域間交流空前頻繁,這一時期也是廣域王權國家形成的關鍵階段,社會的急速發展很可能是早期果樹資源管理和人工栽種的重要動因。
水果類植物資源的利用不同于農作物,從栽種、管理到收獲可能要經歷數年。一方面,這需要相當穩定的農業定居方式作為基礎。另一方面,水果類資源如果要成為經濟體系的補充,該體系的主要糧食供給必須有充足保障。與此同時,遺址之間活躍的交流貿易網也成為先民樂于栽種這些不易保存的水果的重要因素。有學者曾指出,果樹類植物資源與羊毛、牛奶等動物類次級產品類似,被視為重要的“貨幣作物”之一,廣泛出現在早期農業形成之后、城市化來臨之前的社會中,主要用于交換、交易,而非本地消費。以中原地區、長江下游地區為代表,高度發展的復雜農業社會借助區域內部繁榮活躍的交流網,為葡萄屬植物的栽培提供了可能。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早在西方葡萄傳入我國之前,中國本土葡萄屬植物資源的利用就已經持續了數千年,西方葡萄傳入后也并未完全將其替代,二者經歷了長期共存。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青銅時代早期,以中原地區二里頭遺址為代表,一系列農業發展水平、社會復雜化程度較高的關鍵區域很可能已經對以葡萄屬植物為代表的果樹資源進行了栽培。《詩經·豳風》中“六月食郁及薁”的場景,在3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可能十分常見,飄香的瓜果與“五谷”一同為中華文明早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農業基礎。